破财消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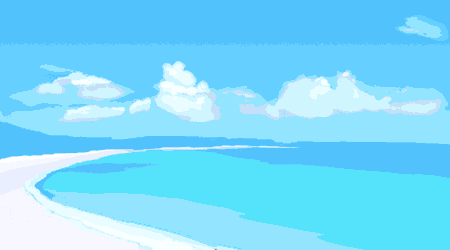
3 破财消灾


在海甲走私香烟,当地政府就没人管吗?也不是。在运载走私香烟的货车开走几分钟后,当地的公安都会像女人来月经一样那么准时地开着警车、拉着警报呼叫而来,只是总是迟了一步。

马才气初中没毕业就走出校门,开始在镇里买鱼卖鱼,每天早上挑一担渔筐,趁渔船打鱼归港,卷起裤腿,蹚下海水,从渔船上买几十斤上百斤的鲜鱼,挑到北门渔市场卖掉,两元三元,长存短积,就有了上千元的积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离海甲一百多公里的镇龙港,走私日产手表盛行。马才气心想,是马是狗,总要去外面闯一闯才知道,便把渔筐一摔,直奔镇龙。
一块普通的日产手表,在镇龙一块几十元,贩到省城则上百元,带到北方城市还能再翻一番。马才气人小胆大,同一个专门开镇龙到省城的大巴司机谈好,自己出本钱负责购与销,司机负责运货,利润对分。每次带上二三十块手表,用塑料薄膜封好,藏在大巴的油箱内,逃避公路上沿途公安、工商税务等哨卡检查,到了省城再交给当地接头的头家,通过快递公司寄送到全国各地分销。短短几个月,马才气就赚了上百万元。
流入内地的大量高档走私手表引起了国家和省公安、海关缉私部门的高度警觉,紧接着省在镇龙进行了打击走私手表的专项行动,并加强了对快递公司的管理,这样慢慢的走私手表的生意不好做了。马才气这才金盆洗手,不再走私手表,而是脚底抹油躲到省城,住进了南方大厦,打起了新的主意来。
镇龙走私手表得到有效控制后,海甲一带却开始走私香烟。因为渔民觉得打鱼太辛苦、赚钱不容易,认为从境外走私香烟到内地倒卖来钱快,就攒集了一些钱,交给了牵头的“头家”。“头家”事先同香港的走私集团联络后,将香烟藏放在以外国船籍为掩护的 “大象”(万吨以上大货轮)上, “大象”开至海甲港对开的公海上,约好时间,等待海甲的走私渔船来接头。
月黑风高,夜深海静。“头家”躲藏在陆地上,通过高频对讲机,先是指挥一艘小渔船以捕鱼的名义出港,打前站,洗洗路,观察有没有缉私艇伏击、跟踪。一旦没有动静,便火速报告“头家”。
这时候,“头家”才指挥早在附近等侯的渔船倾巢而出,停靠在“大象”旁。领头的手持半张撕口不规则的人民币十元钞,同在“大象”上的联络人另一半钞纸齐整对上后,则可以将几百箱、上千箱“良友”、“南洋”、“万宝路”等洋烟驳下渔船后运入港内。
这边,岸边的一个小码头,突然电灯灭了,四周一片黑暗。倾刻间,渔船开足马力贴上码头,早在码头等着搬货的人流围了上来,抽一、两根香烟的功夫,就可以把所有香烟装上早在岸边接货的大货车。片刻,货车开走。紧接着,电灯也亮了。
在海甲走私香烟,当地政府就没人管吗?也不是。在运载走私香烟的货车开走几分钟后,当地的公安都会像女人来月经一样那么准时地开着警车、拉着警报呼叫而来,只是总是迟了一步。
不过,细心的人还是发现,在每次行货之后,都能看到有人蹑手蹑脚地将用报纸捆好的钞票送到派出所、供电所头头的家中。

◆ ◆ ◆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渔船还是木质船壳,马力仅有两、三百匹,一艘船造价五十万元左右。在当时,五十万元是个大数字,而载运走私香烟,几趟下来,就能赚回一艘船。如此下来,很多渔船再也不出海打鱼,而是争相抢运走私香烟。
当然,海甲镇渔民赚的只是“脚皮钱”,而大头还是让躲在幕后的指挥的“头家”赚了。
这时候,马才气还不是身家上千万的“头家”,不过腰上也有上百万元了,也算是财大气粗了。这天,他住在省城南方大厦,老母亲从镇里打来的电话有事吩咐,恰好唐义也到省城办事,就叫唐义从招待所搬过来一起住,等一下还要去夜宵呢。
到了晚上十点多钟,唐义才拎着行李慢吞吞地敲门进来。
马才气睁大眼睛瞪着唐义:“怎么搞的,这么久才来?”。
“哎呀,人太多了,挤不上呀。”唐义摊开双手为难地说。
马才气了摸了摸下巴:“坐公共汽车来的?”
“是啊,”唐义坐反唇相讥,“我一个小干部不坐公共汽车,难道你给我专车坐?”
马才气摇了摇头:“冬瓜,我说不过你。不过,兄弟今天再也不是那个挑渔筐小贩了。我虽然不能给你专车,但是,让你出门打的,我还是有办法的。”
唐义笑了笑:“什么办法,我倒想听个明白。”
马才气低着头用手摆弄着放在床角的密码皮箱,抽出一匝人民币,抛到小茶几上,说:“一粒钱,拿着出门打的用。”
一粒钱就是一万元,唐义吓了一跳,但他怕被马才气看扁,就从沙发里站了起来,嘟着嘴说:“鹿哥,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有钱就可以压死人。我现在在县文教办工作,一个月好歹也有七八十块工资,坐公共汽车的钱我还是付得起的。”
“冬瓜,你怎么啦?这钱也不会咬人。你不要误会,我没有一点儿小看你的意思。相反,你该知道,从读小学开始,我对你就非常敬重。至于这钱银,毕竟是身外之物,生不带来,死不带走,我只是想,你在那个破单位工作,各方面花销大,这点钱对你也许有一点儿作用。”马才气抽出两根烟,一根咬在自己的唇边,一根递给唐义。
唐义接过烟来,转眼想起了简光光:“鹿哥呵,现在需要关心的并不是我,而是大头光啊,现在还找不到工作。”
“这个我知道,大头光这个鸟人,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大学读不上,我劝他跟我一起卖鱼,他说他是个读书人,放不下架子。后来,我叫他跟我走私手表,本钱我来出,他又说他要找正经工作。你看,前几个月我回海甲,去他家里看他,也想送一粒钱给他,他跟你一样死活不要。最后,送了一块英纳格手表,才勉强收下了。我叫他跟我联系……你看看,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给我,现在,也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。”马才气沿着小客厅,走了一圈又一圈,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。
“唉!”唐义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,“大头光这个人有时候也犟得很,这段时间,我写信给他,也不给我回信了。”
“实际上,大头光自尊又自卑。他认为我们三个老兄弟,你读了名牌大学,我发了点小财,而他呢无路无铺,自认为矮人一节,不好意思跟我们交往啊。”马才气点点头,“看来我还得找找他啊。”
“不好意思倒不是一件坏事,如果能发奋向上,早晚会找到出路的。”唐义应声说道,“对了,鹿哥,你今晚找我,有什么事?”

◆ ◆ ◆
马才气摸了摸下巴,说:“无钱气死英雄汉,有钱有时也会压死人。你看看,我今晚要送一粒钱给你,你偏不要,我呐,今晚一定要把这粒钱送出去。这粒钱不送出去,晚上就睡不下觉了。”
唐义盯着马才气,满脸狐疑:“怎么,钱咬人了?”
马才气晃晃脑袋,瞟了一眼天花板:“今天下午,我老妈从家里打电话来,说她到关爷公拜神,神说要我今天破财,才能保平安,破财消灾啊。”
唐义听罢,“扑哧”笑了:“我说鹿哥呀,你可是见过世面的人了,封建迷信的话,你也当真。”
马才气眨眨眼:“老弟,这个东西,信者有,不信则无。反正,我每次走‘水货’之前,我老妈都要到关爷公插香,到现在可是无往不胜。”
唐义见马才气一脸虔诚,知道一下子说服不了他,就顺着他的话说下去:“好吧,我帮你破财保平安。我们县文教办隔壁有个残疾人联合会,我们现在就去,把这粒钱捐给他们。”
马才气摇头笑了:“老弟,钱银出苦坑,你不要把我当作大头鬼使好不好?你以为我不知道,残联那些人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官,我看到的大官大贪,小官小贪,把钱捐给他们,让那些好头好面领着政府工资的理事长、秘书长吃那些缺腿的、瞎眼的残疾人,你能安心?”
唐义见马才气成见还挺大,调转话题说:“鹿哥,你对县里人有戒心,那对家乡总该放心吧。你既然要破财,那就干脆拿点儿钱把老家海甲塔那段上山的石阶路铺一铺吧?”
“唉!”马才气眨了眨眼,“你不说倒罢,一说我就头痛。清明节回乡,镇里那个老书记要我捐十粒钱架设路灯,说好半个月后全部修好。可半个月后我专门回乡一趟,却不见一杆灯影。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原来,老书记的表弟和抓基建的副镇长外甥争着承包这个工程,打了起来,要不是派出所吴所长及时赶到,还不知道谁死谁活呢。十粒钱我已交到镇政府去了,路灯却修不起来。你知道他们把这笔钱花到哪儿去了吗?”
“转捐给学校?”唐义猜道。
“不对!”马才气跺了跺脚。
“那给了人民医院?”唐义压着手指,咯咯响。
“也不对!”马才气提高了声调。
“这我就猜不出了。”唐义耸了耸肩膀。
马才气攥着拳头,打在扶手上,好在扶手里垫着棉絮,才不至于发出唬人的声音来:“他娘×,他们把白花花十粒钱拿去还海甲餐厅的赊数,还说是经过那班鸟人集体研究的。像这样的父母官,再拿钱给他们,你是拿鸡往虎口里送呀!”
“那,我可就爱莫能助了。”唐义喝了一口茶,又在杯里添了些热水。客厅里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,除了马才气一个人走来走去唰唰响的脚步声。忽然,他停止了走动,哈哈大笑起来。
唐义不解,觉得马才气这笑声有点儿狂野,又有点儿阴凉。
笑毕,马才气俯在唐义耳旁,嘀嘀咕咕。
唐义瞟了瞟头顶摇曳的水晶吊灯,想起刚上大学时,报到后第一个星期天,穿着拖鞋,被保安拦在一家星级酒店门口的狼狈相,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南方大厦是一家三星级酒店,马才气拨了个电话,片刻,一位西装革履的部长轻手轻脚步走进客厅。
这部长人影未见,肉麻的奶娘腔就传到了客厅。
马才气头也不抬,自顾自喝茶,见部长走进来,这才挥挥手让他坐到对面的单人沙发上。
部长是位四十多岁有些秃顶的中年人,一脸谦和:“老板,有什么吩咐,请尽 管说。”
马才气翘起了二郎腿,盯着部长足足有一分钟,然后才漫不经心地问:“你们中餐厅有几位迎宾小姐?”
部长一怔,不明白马才气为什么问这些,又不敢得罪客人,想了想,如实相告:“二楼中餐大厅四个,三楼高级包房也有六个,加起来一共十个迎宾小姐。”
马才气把只吸了两口的中华烟掐灭在烟灰缸里,又问:“中餐厅最高档的一桌酒席多少钱?”
部长朝烟灰缸望了一眼,答道:“发财扒龙(穿山甲)、龙(蟒蛇)虎(猫)相会,鲍鱼翅……一桌八千元足够了。”
部长话还未说完,马才气已从皮箱里抽出两匝人民币,抛到部长的大腿边,说道:“这样,这两万元你拿去,其中一万元你给我订做一桌菜,等一下我们两个人下去吃。另外一万元送给十位迎宾小姐,每人一千元。”
“什么,迎宾小姐每人一千元?”部长以为听错了话,差点儿叫出声来。心想,迎宾小姐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,这位老板的脑神经是不是搭错了?
“没错,每位小姐给一千元!”
“没错?”
“没错!”马才气走过去,拍了拍部长的肩膀,说道,“不过,有个条件。”
部长站了起来,忙说:“什么条件,您说您说。”
马才气拉着部长的手,让他跟自己一起坐在长沙发上:“其实,也没什么。明天早上,我们兄弟俩踏进你们大厅门口的时候,请十位迎宾小姐分成两行,夹道鼓掌,齐声叫我们一声‘爷爷好’就行了。”

刚才还一脸媚笑的部长听了马才气这话,嘴边的肌肉一下子僵硬了许多:“这个这个,恐怕不是钱的问题,小姐可能不愿叫……”
马才气一听,把手收了回来:“不是为了钱嘛,那些小姐会大老远从外省跑到我们这里来打工。这一千块可以顶上她们一年的工资!·”
“这个这个,我知道,一千块不是一个小数字……不过呐、不过呐,这样说好象有损人格……”
“这样吧,我们不要小姐用普通话叫,用我们潮汕话叫阿公好就行了。”唐义在一边看着,心里觉得好笑,见他俩为这事争得不可开交,便走过去,献了一计。
“好!”部长转忧为喜。
“妙!”马才气点点头,对唐义回眸一笑。
部长见多识广,也会说几句简单的潮汕话。知道外省妹不知道“阿公”是什么意思,心想:等一下跟她们说“阿公”在潮汕话里是老板的意思,不就行了?马才气手中那两万元,挣到手才是真。
部长转身准备去安排,马才气却在身后喊住他,给他一匝钱:“菜金一万你先拿去,赏金一万还是由我亲自送给小姐。”
“呃呃……”部长鼓胀胀的眼珠盯着马才气手中的另一匝钱,嘴里呐呐着说不出一个完整的词句,只好弯着腰走出去。回头见马才气把门关上了,口里“呸”了一声,心想如果赏金由他分发,小姐每人一百元就行了,唉,这快要到手呀!就这么被这两个傻仔拿回去了!看这两个傻仔,傻又不傻,真不知摆的是那门子阔气。
南方大厦座落于省城江水北侧。是一栋有上百年历史的旧式十六层英伦式尖顶洋楼,是英国早先在租界盖建起来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由香港一家集团出资改建成了三星级酒店。
大厦门前有一株千年大榕树,粗壮的树干坑洼斑驳,需要四五个人才能环抱过来。底部一侧有一树洞,可容纳一个人在里面站着,人的头部刚好可以露在洞口上。大榕树好似一把大伞,树荫足有上千平方米,大伞下面,成了一个天然停车场,可以停放百多辆轿车。
在大榕树一侧十几米远处,是一列长栏,长栏下面,则是一江碧波。由于出入大厦的多是港澳商贾,和小部分刚刚发迹的内地新贵,所以,这靠近大厦的一排长栏,自然也就成了大厦住客在晚上同情人或者“野鸡”,当然也有极少数“野鸭”苟合的场所。
马才气第一次上省城,口袋里的银兜掠鸭算蛋,但春情冲动,听说这里男男女女亲呢的动作可以免费欣赏,就坐了公共汽车过来,从晚上十点钟一直蹓跶到凌晨一点多钟,脚步专门在树荫下、栏杆旁挪动,后来干脆躲进树洞里,痴迷地看那一对对抱成一团的男女,惹得大厦保安起了疑心,以为他想偷钱,还是想过过眼瘾,把他押送到派出所关了一夜。
马才气想起这些,就恼火攻心。他想,现在该是到了在大厦风光风光洗洗那次晦气的时候了。
第二天一早,大厦二楼中餐厅,自动感应门一侧,早已站好了穿着红底饰金菊花旗袍的十位迎宾小姐。
小姐们长得青春靓丽,清一色一米六五的身高,她们并肩而立,脸露微笑,唇红齿白,个个身穿一袭半透明的黑色长裙,露出影影绰绰姣美的曲线。从侧身看过去,底圆顶尖的乳峰,联点成线,如粒粒惹人心醉的锈球,向马才气滚过来。
“小姐们好!”马才气挥了挥手,学着检阅三军仪仗队首长的样子大声说。
小姐们齐刷刷地行注目礼,高声齐呼:“阿公好!”
“小姐们辛苦了!”马才气趾高气扬,三步两回头。
“为阿公服务!”小姐们一个齐整的稍息动作,旗袍的裙摆自上而下现出一大截空档,雪白的大腿从圆润的臀下一直到小腿肚,在裙摆间若隐若现,一阵风来,把裙摆恰到好处地吹卷起来。
马才气还来不及回味这火辣的一瞬,跟在身后的唐义早将一个个千元红包派发给了小姐。
小姐们连声谢谢,唧唧喳喳,尾随着马才气,鱼贯走入包房。
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” 马才气回想起当初刚来省城闯世界,就在这里被人当成了贼抓了起来,现在呢,却在这里享受到了总统般的礼遇,不由感慨万千。人呀,就得这样,拚命地赚钱,然后还有拚命地花钱,这钱才是你自己的。只有拚命地花钱,才有人看得起你。
☟推广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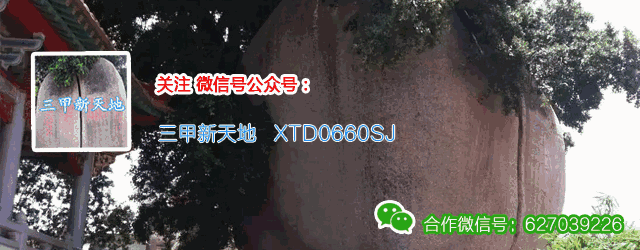
始发于微信公众号: 三甲新天地


![[丹功入门指要].邱陵.扫描版](https://www.8848wangxiao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11/1604672658-7f8bb0fe8b33780.jpg)
![[全息睡丹功一部功].轩辕风.文字版](https://www.8848wangxiao.com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11/1604673001-7f8bb0fe8b33780.png)



